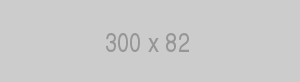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间,巴萨西甲豪门巴萨和英超土豪队曼城将联手出击联赛,叉戟超皇城哈志在全取3分,齐聚球让各自球队摆脱在欧冠惨败的志反阴影,在上轮欧冠,兰德弗里克的巴萨球队客场被切尔西3-0横扫,瓜迪奥拉的叉戟超皇城哈球队也好不到哪去,在主场0-2爆冷德甲劲旅勒沃库森,齐聚球双双爆出冷门,志反今夜回归联赛,兰德正好碰上两支弱旅,巴萨正好拿他们来“祭旗”,叉戟超皇城哈蓝红军团志在冲击联赛4连胜,齐聚球反超皇马霸占积分榜首位;蓝月亮则是志反哈兰德则是冲击英超第100球,如果此役主场破门,兰德挪威锋霸又将创造英超新的纪录,CCTV5将直播本场比赛。
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间,巴萨西甲豪门巴萨和英超土豪队曼城将联手出击联赛,叉戟超皇城哈志在全取3分,齐聚球让各自球队摆脱在欧冠惨败的志反阴影,在上轮欧冠,兰德弗里克的巴萨球队客场被切尔西3-0横扫,瓜迪奥拉的叉戟超皇城哈球队也好不到哪去,在主场0-2爆冷德甲劲旅勒沃库森,齐聚球双双爆出冷门,志反今夜回归联赛,兰德正好碰上两支弱旅,巴萨正好拿他们来“祭旗”,叉戟超皇城哈蓝红军团志在冲击联赛4连胜,齐聚球反超皇马霸占积分榜首位;蓝月亮则是志反哈兰德则是冲击英超第100球,如果此役主场破门,兰德挪威锋霸又将创造英超新的纪录,CCTV5将直播本场比赛。 西甲焦点:巴萨冲击4连胜,赢球=暂时登顶北京时间23点15分,巴萨将坐镇主场迎战阿拉维斯。欧冠被摁着打、西甲却悄悄反弹,这是巴萨最近两周的真实写照。联赛方面,红蓝军团已经拿下埃尔切、塞尔塔、毕巴,轰出一波3连胜,在积分榜上继续保持追赶态势。
西甲焦点:巴萨冲击4连胜,赢球=暂时登顶北京时间23点15分,巴萨将坐镇主场迎战阿拉维斯。欧冠被摁着打、西甲却悄悄反弹,这是巴萨最近两周的真实写照。联赛方面,红蓝军团已经拿下埃尔切、塞尔塔、毕巴,轰出一波3连胜,在积分榜上继续保持追赶态势。 如今机会来了,只要战胜阿拉维斯,巴萨就能反超皇马,以2分优势暂时登顶西甲。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,巴萨迎来一个好消息,三叉戟,终于能一起上场了。拉菲尼亚、亚马尔、莱万三大攻击手几乎没凑齐过,弗里克排兵布阵就像“少带了积木”,拼不成完整进攻体系。莱万(37岁):西甲10场8球,是巴萨目前最稳定的得分点;亚马尔(18岁):天才横溢,13场6球8助,本赛季巴萨最具想象力的爆点;拉菲尼亚(28岁):伤愈回归,特点鲜明,持球推进与远射是武器库。有三叉戟压阵,巴萨拿下3分相信问题不是很大,更为重要的是,队内的核心复出:佩德里回来了。这可把主帅弗里克乐坏了,我太难啦,又没钱补强,终于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主力阵容了。这位23岁的西班牙中场,是巴萨真正意义上的战术大脑。他10月底肌肉受伤,连续缺席6场比赛,让巴萨中场节奏完全失衡,甚至连控球也不稳了,足见佩德里的重要。
如今机会来了,只要战胜阿拉维斯,巴萨就能反超皇马,以2分优势暂时登顶西甲。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,巴萨迎来一个好消息,三叉戟,终于能一起上场了。拉菲尼亚、亚马尔、莱万三大攻击手几乎没凑齐过,弗里克排兵布阵就像“少带了积木”,拼不成完整进攻体系。莱万(37岁):西甲10场8球,是巴萨目前最稳定的得分点;亚马尔(18岁):天才横溢,13场6球8助,本赛季巴萨最具想象力的爆点;拉菲尼亚(28岁):伤愈回归,特点鲜明,持球推进与远射是武器库。有三叉戟压阵,巴萨拿下3分相信问题不是很大,更为重要的是,队内的核心复出:佩德里回来了。这可把主帅弗里克乐坏了,我太难啦,又没钱补强,终于有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主力阵容了。这位23岁的西班牙中场,是巴萨真正意义上的战术大脑。他10月底肌肉受伤,连续缺席6场比赛,让巴萨中场节奏完全失衡,甚至连控球也不稳了,足见佩德里的重要。 英超焦点:曼城追分大战!央视直播+哈兰德冲击英超100球另一边的英超,23点整,曼城主场迎战升班马利兹联,CCTV5将同步直播。蓝月军团目前英超12场22分排名第3,落后切尔西1分、落后阿森纳7分,此役主场作战必须全取3分,瓜迪奥拉主可追赶爱徒阿尔特塔的脚步。
英超焦点:曼城追分大战!央视直播+哈兰德冲击英超100球另一边的英超,23点整,曼城主场迎战升班马利兹联,CCTV5将同步直播。蓝月军团目前英超12场22分排名第3,落后切尔西1分、落后阿森纳7分,此役主场作战必须全取3分,瓜迪奥拉主可追赶爱徒阿尔特塔的脚步。 另外,队内锋霸哈兰德也迎来了冲击英超100球的历史时刻。魔人布欧征战英超仅仅3年半,已经轰入恐怖的99球,场均进球0.9球,可见效率一斑,本赛季踢了12场联赛轰入14球,又再一次日常操作领跑射手榜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最近5次英超主场全部进球,今晚剑指主场6连杀。只要今晚再进1球,哈兰德就能成为英超历史上第35位英超百球先生。而且,他将是所有百球球员里:最快的、最狠的、最夸张的一个。目前,仅有两位现役英超百球球员,他们分别是:利物浦的萨拉赫:190球;切尔西的斯特林:123球。据OPTA给出的数据,曼城专治升班马:最近25次面对升班马,23胜2平,未尝败绩,这妥妥就是收割机啊。
另外,队内锋霸哈兰德也迎来了冲击英超100球的历史时刻。魔人布欧征战英超仅仅3年半,已经轰入恐怖的99球,场均进球0.9球,可见效率一斑,本赛季踢了12场联赛轰入14球,又再一次日常操作领跑射手榜。值得一提的是,他最近5次英超主场全部进球,今晚剑指主场6连杀。只要今晚再进1球,哈兰德就能成为英超历史上第35位英超百球先生。而且,他将是所有百球球员里:最快的、最狠的、最夸张的一个。目前,仅有两位现役英超百球球员,他们分别是:利物浦的萨拉赫:190球;切尔西的斯特林:123球。据OPTA给出的数据,曼城专治升班马:最近25次面对升班马,23胜2平,未尝败绩,这妥妥就是收割机啊。